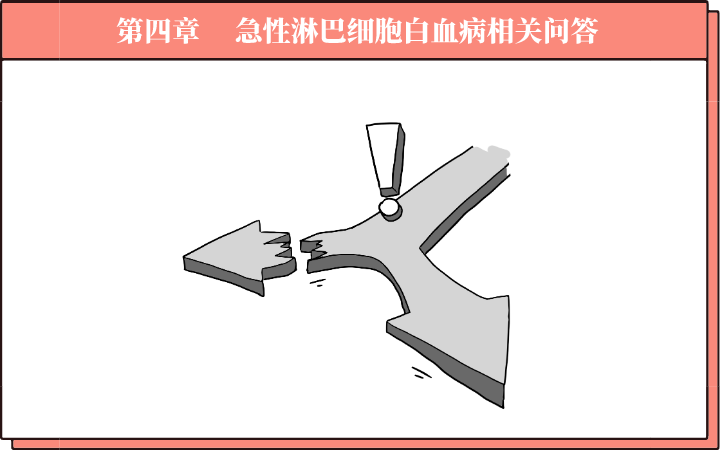虽然已经有一些关于尊严疗法的研究,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探索。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谁最有可能受益于尊严疗法?尊严疗法所起到的治疗效果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衡量尊严疗法的影响和益处?
一些临床工作者已经开始将尊严疗法应用于更广泛的患者,而不只是应用于晚期癌症患者。这表明,尊严模型本身的应用可能超出了癌症和临终的范畴。读者可能会记起,包含在尊严模型中的主题和子主题十分普遍,包括身体上的影响(疾病相关忧虑)、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尊严条目),以及临终患者心理和灵性方面的影响(尊严维护条目)。虽然这并不是说该模型可以不加区别地应用,但是从其有效性来看,它肯定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人类经历范畴。我们研究小组已经将尊严疗法试验性地应用于住在护理之家的老年人。开始这个试验的原因是因为临终患者和老年人在存在方面有共同需求。前者处于濒死状态,后者正迈向生命的终点。虽然我们的结果(将很快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文献中)表明,在虚弱的老年人中实施尊严疗法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对于老年人这一群体来说,尊严疗法是一种可行的干预[7]。
我们在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患者中使用尊严疗法有一些经验。虽然讲话能力通常是一个显著且影响语速的因素,但是耐心、创造力以及调整——例如应用各种促进式沟通——能够使这些患者拥有积极的尊严疗法经历。在一个实例中,一位患有ALS的先生,仍然能够用手打字提供电子版的尊严疗法文档。这就让他能够通过键盘进行编辑,并且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完成文档修订。
我在澳大利亚的同事在西澳大利亚运动神经元病(MND)协会资助下,正在研究如何将尊严疗法应用于运动神经元病的患者。虽然许多人认为,尊严疗法可以应用于此类人群中,或者尊严疗法正应用于非急性临终情况下的患者(例如,女性乳腺癌的3期或4期),然而就我所知,尚无任何资助的临床研究验证尊严疗法在这类特定患者中的作用。
尝试研究尊严疗法的研究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整个科研设计和选择结果测量工具。我们目前完成的随机对照研究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识别研究组间的差异[5]。然而,当患者的基线悲痛程度很低时,通过心理测量很难看出显著的变化。换句话来说,只要研究方案旨在说明干预前后的变化,而不是干预后患者各方面的临终体验,证实其有效性将取决于被研究人群的起始悲痛程度。引用医学类比,说明一种药物的退热能力或促进骨骼愈合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分别取决于发热和骨折的出现。
有一些情况,像同时患有临床抑郁、谵妄,或是焦虑的患者,的确有些东西已经“坏了”,需要治疗和修复。那些并发症让他们适用于实证研究,即应用传统方法实施临床研究,应用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以及标准的统计方法。然而,这用于濒死患者是有挑战的,他们并不能等同于“坏了”的东西。沉重的心情、悲伤的灵魂、面临死亡的痛苦,这些到底是通往死亡路上的并发症,还是我们人性和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的体现?或许我们的治疗需要包含见证、肯定和治愈的观念,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或治疗并发症。
这些问题貌似本质上是哲学的,但它对研究者的启示却很实用。一些尊严疗法参与者说,尊严疗法在生命接近死亡的过程给他们带来了平静;另一些则允许他们的配偶在他们死后寻找新的生活伴侣。一位患者想寻求女儿的原谅,因为告诉女儿父亲的身份为时已晚。另一位女儿告诉我们,她父亲唯一一次表示爱她并且以她为荣是在尊严疗法的文档里。这些结果很难量化,尤其是应用心理测量工具时。然而,这些结果的意义深远且切实。尊严疗法的研究者应该努力获取这种数据,虽然这在绝对的量化范例中不容易获得。定性研究和测量试图捕捉患者自我价值、平和、平静、尊严、意义、灵性健康,或存在的焦虑,这些都是重要的课题研究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