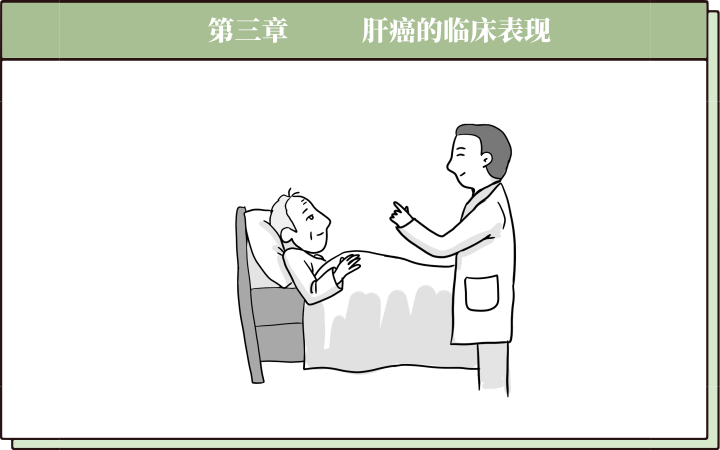大约一年前,我有幸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开办尊严疗法培训班。开始的前一天,一位学员找到我,她说她对于尊严疗法可能通过志愿者来实施感到非常兴奋。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应她,我的语气肯定出卖了我。直到研讨会结束,我们再次联系,她说:“我明白你当初为什么犹豫了。”事实上,在志愿者或家属是否可以实施尊严疗法这件事上,我的确犹豫不决。
毫无疑问,家属和志愿者在临终生命支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尊严模型的元素有很多,这些元素能够告诉他们如何满足临终患者的心理、灵性以及存在感的需要。从这个模型中,我们知道重视和肯定一个人的人格是高质量临终生命关怀的一个重要因素。询问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过去、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尊严疗法所包含的很多问题是非常好的信息传递方式,借此传递他们现在怎样、过去怎样,以及那些他们必须要表达的。这种价值通过倾听者在场和专注地倾听以及对患者所分享的事情的理解和欣赏这些简单和有形的方式传递。
然而,我认为让志愿者和家属实施尊严疗法有一些障碍。首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尊严疗法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一样是需要技巧的,这些技巧需要长时间仔细和深入训练。人们经常认为尊严疗法仅仅是阅读问题提纲(即尊严疗法问题协议)和被动的记录人的回应。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本书的读者应该明白,尽管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治疗师必须能够非常熟练地诱导患者回应和识别重要的问题,并让患者高度参与治疗过程,以此减轻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将患者所述整理到一份结构紧密并且有意义的传承文档中。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或经过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才能实施尊严疗法。我培训过社会工作者和姑息治疗护士,他们也能成为技术娴熟的尊严治疗师。在我看来,家属会有一个额外的挑战使得他们对所爱的人实施尊严疗法特别困难。任何失去过至爱的人都知道,看到自己亲近的人(可能那些人影响了或者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死亡时,那种强烈的、心痛的感觉。这个经历引起一连串的感情释放——痛苦、疼痛、迷失方向、悲伤——但是它唯独做不到客观。实施尊严疗法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是很重要的。治疗师需要注意整个治疗过程,他们必须掌控时间,确保患者能够在一个不超出他们精力和能力范围的时间内完成访谈。治疗师需要掌控患者是否偏离治疗主题。治疗师必须总是保持温和有礼貌,同时又随时要准备好进行引导,达到帮助患者实现他们参与尊严疗法的目的。
虽然可能不明显,但尊严治疗师在实施尊严疗法时需要进行巧妙的平衡,这再一次超出家属可能做到的范围。一方面,治疗师必须在当下给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考虑到能够让患者讲出各种他们希望包含在传承文档里的内容的机会是有限的。一个娴熟的治疗师能够在不牺牲治疗质量的情况下达到这种平衡。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特定的传承信息很难被表达出来的心理原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往往起源于矛盾的人际关系或一些没有解决的内心问题。例如:
一位63岁的老先生在他的采访早期透露,他的父母在对他们的孩子和彼此的情感上很矜持和含蓄。这种沉默寡言地表达感情也是他的一个特质。现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他使用尊严疗法同妻子和两个女儿分享他的回忆、希望和梦想。虽然他能够很容易地讲述故事和丰富的传记,但是这些信息包含很少对家人的情感。注意到这一点后,治疗师建议“彼得,你好像一直都很难告诉家人你对他们的感觉。鉴于这是你的尊严疗法,你觉得今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吗?”提供这个方式,即使是柔和地,也是相当冒险的治疗策略。然而,一个娴熟的治疗师能够填补治疗的空缺和机会,同时让患者决定如何进行下去。在这个例子中,彼得回应道:“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爱他们,过去爱他们,并且一直尽全力地爱着他们。”